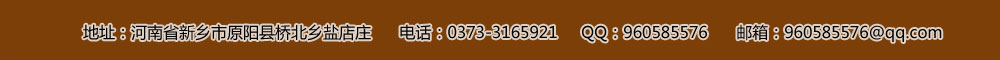张玉舌尖上的故乡
舌尖上的故乡
一、豆蔻梢头
今天有人在小区里叫卖豆角:“新鲜的荚荚,本地荚荚。”我探头一看,果然,是那种绿地紫纹的花豆角,清凌凌地带着水气,嫩得仿佛能掐出汁液来,于是迅速称了几斤,想吃一顿焖面。回到家,我洗洗手择豆角,它委实太鲜嫩了,连筋都不用抽,我举起一根豆角放在鼻尖,闻到熟悉的草叶的气息,让我想到河流和篱笆,晨风和村庄。这样的气息让我感觉到胃在温柔地蠕动,有人在喊我的乳名,光阴在北寨以北随意聚散,春天就不期而至了——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,这使每个季节都在九州大地上各行其道。有人在 蝴蝶开满院子
爷爷锄断一棵金针
伤口渗出碧绿的汁液
面对豆蔻的泪水
这诗现在看起来,有一点无病呻吟的味道,因为当时的我年轻得就像豆蔻,我并不知道春天终会过去,金针会谢,豆蔻会枯萎,种豆角的老人会离我而去。豆花开了又落了,一茬茬的豆角挂在梢头无人采摘,直到豆荚开裂,滚圆的扁豆和玉米叶子一起散落在秋风里,再也没有人给我吃豆角焖面了。
二、浆水的倒影
过了清明,就可以发酸菜了,往年的这个时候,奶奶就开始淘洗家里的黑陶大瓮,然后把茴子白洗净切碎,略煮片刻,拿笊篱捞入瓮里,再倒进晾好的开水和引子,盖严了,过个几天一揭开盖子,酸菜的清香就扑面而来。酸菜最好下饭,夏天拌凉面能开胃生津,冬天包饺子去油除腥,是农家的清淡美食。然而我最怀念的,是酸菜的衍生物,或者说发酸菜时的副产品——浆水。
浆水是什么,是菜叶和酵汤在陶瓷中打坐沁出的甘露,是草木之精华经过了人间五味锻炼的佳酿,它比酒清冽,比醋甘甜,它的味道是乡土的、江湖的,稍纵即逝在舌尖。我最喜欢喝浆水,夏天热得狠了,跑进东屋里揭开酸菜瓮,舀一勺浆水大口吞下,一股凉意从头到脚激射而下,不禁打个寒噤,瞬间头脑清凉。吃灌肠时倒半碗浆水,加芥末油,芳香清辣美妙难言;它可以制作许多美味佳肴,调凉菜时加一点,味道甘酸清爽;略放点白糖,是消暑解毒的饮品;如果把浆水用葱花炝锅,再加入切得细细的手擀面,就成了美味的浆水面。
做浆水,是我奶奶做得最好,因为她老有奇思妙想,酸菜瓮子里内容丰富,经常会加一点切碎的野菜,灰藋、甜苣、萝卜缨子、甚至还有槐花,她都往里面放过;下完面的面汤,她总要澄清了,晾凉了,细细地滗进浆水瓮中,像浇灌花草一样精心。因了这些点缀,她的浆水菜酸香绵软,回味悠长。小华家的浆水一股汗酸味,我喝过一次,令人掩鼻;三大爷家的浆水则是很凶狠辛辣的酸,味道太烈,三大娘嫌太酸,撒进一大把盐,结果更酸了,又笑又气。吃惯了浆水,我便不喜欢醋的味道,嫌它黑而浊。
有一年我在老家过暑假,每天在山里疯跑,上了火,嘴角起了好多大泡泡,那天我午睡醒来,头一晕就栽倒了,是严重的中暑。爷爷奶奶急得要死,我爷爷赶快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,这一天正好我父亲也回来了,他一进门,奶奶就拉住他急急地述说我的病情,然而父亲看到我脏兮兮蓬头垢面的样子,一声怒吼之后便是劈头盖脸的耳光,我的血顺着嘴角流下来,昏沉中我只听到奶奶撕扯他的哭声——因为种种原因,我从小和父母关系很差,挨打是家常便饭。到了晚上,我的头疼好了些,但还是不想吃东西,奶奶给我调了一碗凉粉,又倒了一碗浆水,告诉我这个最是下火,一定要喝完。我坐在门前的石阶上,就着月光吃凉粉,面对一大碗浩浩汤汤的浆水,真的有茫然之感。月光照在院子里,老梨树下有零散的昆虫鸣叫着,金针菜的叶子泛着银光,凉粉晶莹得令人心碎,月亮睡在浆水中,金黄浑圆,我的泪水落进去,融在它的笑脸中,我忽然感到心里安静下来,有一种不知名的东西在我身体中生发。
那年我十五岁,那是我在北寨以北度过的最难忘最宁静的一个少年的夜晚,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在浆水碗中看到了命运的倒影,我想我不能否认。
今年我三十五岁,最疼我的爷爷于年前去世,只剩下奶奶伶仃在日新月异的时光中,独自惶惑地面对残年。她已经不能再发酸菜了,马上又是清明,不知爷爷在那边,会不会想念浆水。
前几天我在超市买了几袋浆水酸菜,拿回来调凉粉,酸得发涩,咸得发苦,满满的都是味精和醋酸的味儿,吃得倒胃。奶奶发的浆水酸菜,不是我现在吃的这种袋装速食可以比的;水质、季节、心情、容器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它的味道,那种酸甜的、清凉的、沧桑的祖父母的味道。
对我来说,浆水始终都流淌在那个年代,它不仅是一种能消暑清火的食品,也是一种光华,一种乡愁,一种亲情,它亘久不变。
三、思念一种野菜
今年春天,爱香送我一大袋甜苣菜,是她在交流任教的乡镇小学附近挖到的,我很高兴。
我小时候也挖过甜苣,那时候我们管它叫苦苦菜,后来才知道它的大名是叫甜苣。苦和甜无疑是两个相反的概念,那么说这苣菜到底是甜的还是苦的,这两个名字到底哪一个更符合实际?我认为它们同样真实,同样准确。
这种菜紧贴着地皮生长,要完整连根拔起很困难;我左手握住它的叶子,右手拿铲子一挖,菜茎便从贴地的白梗处断开,离了根的菜叶会在脉络中沁出白色的乳汁,我偷偷用舌头舔过,却被苦得呲牙咧嘴。这个时候,它当然是应该叫苦苦菜的,我相信它的苦是用来保护自己,好让馋嘴的牛羊不敢打它的主意,或者说这苦涩的乳汁是它流出的泪水,它为不可知的命运而哭泣。
我们把它挖回去,择好洗净,开水汆熟,然后泡进冷水,等到水色变为深黄,便重换清水,如是几次,直到水色清绿,就算泡好了;奶奶把它切碎了,加盐和浆水,洒一点麻油,香气袭人,有时还放杏仁,味道鲜美至极。这个时候,它就该叫甜苣了吧。新鲜的甜苣拌了蒜泥,一清二白十分夺目,那扑鼻的香气留在我鼻尖,多少年挥之不去。这种滋味的变幻,绝不仅仅是舌尖的感觉,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升华,一种深入浅出的演绎,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,那么它必然是“苦尽甘来”,这是人生的大道,有哲学意味。
那时候的地里总是一大片一大片浓密的野草,许多野菜混在其间。不仅有甜苣,还有灰藋和玉谷,苜蓿和白蒿;挖菜的多是女人,也有几个小姑娘,铁铲入土的声音嚓嚓不绝。小华手里的菜满了一把又一把,她把篓子捺满了,还要一把一把沿着系子堆上去,塞成一座绿色的小山;我就不行,挖了半天还是半篓菜叶——我天生不擅活计,不光是速度跟不上,质量也很差,譬如说同伴们都会尽量将甜苣连根挖起,我就办不到,只能铲到菜叶子;而那些埋在地下的白嫩的菜根,才是甜苣的精华,是最为清甜的部分。我瞪大了眼睛找菜,可是天生的笨人没法子,脚踩住了都看不见。
近年来,人们的生活好了,大鱼大肉的饮食让许多人营养过剩,野菜作为绿色健康食品,重新走上人们的饭桌。在星级酒店,它们被精心炮制呈于贵客,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。我吃过这样的甜苣,也不能说不好吃,但是总缺一点什么,也许是作料太多了,烹饪太精细了,反而失去了本真的味道。
我在思念甜苣,想来想去,想不到可供书写的文字。关于甜苣的歌谣,我印象中没有;周作人说的“荠菜马兰头,姊姊嫁到门后头”这样深情的词句,我不曾听闻;也许荠菜是野菜中的贵族,而甜苣是平民,此身只合江湖老。它代表一个季节,一个时代,一个诗意的存在,它生长在我的记忆里,永远不会消失,它告诉我,苦涩是生命的元素和本怀。漫长的岁月中,年少的甜苣源源而来,无边无垠的清香中,我化身为同样苦涩卑微的野菜。
我拿了爱香的甜苣,洗净烫熟放在冰箱里,原想着储存一段时间的,没想到几天就吃得精光;可是吃甜苣的馋念一旦被勾起,却无法轻易消除,于是自己去挖。
可是我找不到甜苣生长的地方。藤条篓如今何在?泉水溪如今何在?一望无垠的田野上疯长的青草何在?教我辨识野菜的爷爷又何在呢?一切都没有了,连同我的乡愁和年少情怀,乡土只合在梦中浮白——为了野菜,我又回到北寨……好在还有北寨。
我走的那么远,终于在村外的原野上找到一大片野菜,沙蓬、山韭、婆婆丁,甚至还有小蒜。甜苣已经长大了,不再鲜嫩,开出了淡黄的花朵,不能采了,茵陈却正当时。我埋着头专心挑菜,初夏的阳光从山杏枝头漏下来,几只蝴蝶跌跌撞撞地飞过,草尖的露水滴下来,润到了菜根,我有些寂寞,于是直起腰身。
这是春末夏初的故事。
四、 一碗面皮
外地人叫凉皮的东西,晋中叫面皮,我以为面皮这个叫法更准确,因为它本来就是面做的嘛,而且它并不是只能凉拌着吃,也可以炒的,所以还是叫面皮更好。面皮应该是北方小吃,华北大多地区都常见叫卖,南方则不常见,据说陕西凉皮最美味,但是我去西安时吃了几次,感觉没有山西的好吃,不知是不是口味不惯的原因。
我小的时候,父母租居在城里,房东老太就是卖面皮的,有次我到她家去,见她在大盆中揉洗一团白白的东西,我问:“婆婆,这是什么?”她说,面啊,洗出来做面皮。我大跌眼镜,原来面皮是洗出来的。我好奇地蹲在地上看她洗面团,一会儿,盆中的面汤变得浓白,老太拈起一大团蜂窝状的东西,笑着告诉我这个是面筋,很好吃,待会儿蒸熟了给你吃一碗。说着话她转身揭开冒着热气的笼屉,熟练地把面汤舀进去,开始蒸面皮。但我只能咽下口水离开——父母是严禁我们吃别人家东西的,何况是房东了,我最终也没有吃过老太太的面皮。但是我记住了那个温馨的下午,那个慈和的笑脸,以及制作面皮的流程:将和好的面反复揉洗,直至面团一点粉糊也无,只剩下清爽的脉络,然后上笼蒸制,那是暗合人生真谛的冶炼之旅,面皮在千锤百炼中成型,如同我们脸上这一张。
那个时候我常吃面皮,最喜欢电表厂出口处的一家,她家面皮不是许多张摞在一起的,而是一张一张卷好,整齐地码放,有食客了,那女人便麻利地抓起一个皮卷子,操刀切好,然后娴熟的放卤汁和调料;面皮淡黄温润,卤汁红褐香浓,切碎的葱花总是新鲜嫩绿,令人食指大动。女人的动作也赏心悦目,她拿一把短柄厚刀,切皮子时飒飒有声,撒盐、倒醋、舀卤汁、淋蒜水,最后拈起两三根条子往辣椒油中一蘸,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般。那碗中色彩鲜艳,各种香气纵横交错,间或咬到一根黄瓜丝,清脆如黄鹂鸣叫。
很多年了,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清爽的面皮。
近年来,我的口味渐趋清淡了。吃面皮,我不再加卤汁,甚至连芝麻酱都不要了——只滴些许麻油和蒜水,加盐醋;这样的简易面皮,却能让我吃得轻松。在这个舌尖时代,我以为,除了那些香辣咸鲜的重口味,也应该用这种极清极素的轻口味去调节一下;就像我们的面皮,长久被各种迎来送往的寒暄弄得僵硬,也需要放松几天。我是个不善应酬的人,遇到面皮和里子难以两全的事,总是不知所措,逞口舌一时之快,大抵是年少轻狂吧,那日子真是叫嚣东西隳突南北,所以回忆青春,必定感叹惟有爱与美食不能辜负。
我常常寻找过去的小吃,冲着记忆中那些年少的口腹之欲而去,收获的却往往是失望。那些曾经惊艳的味道,说到底,它们就是人与事及时光这三维的叠加,它们没有过去,没有将来,惟有现在,惟有那一刻的情怀。原来,我是这样一个落魄的追梦人,我吃的不是面皮,是老街,是故人,是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。它们已一个个散落于时间深处,那些香气和美味,自然一起风流云散。当然,总有一碗面皮,一直在似水流年中等待,时不时低低唤我,在心情焦躁时,在酷暑热浪中,去吃碗面皮,比什么都美妙。
五、饼中岁月
我弟弟现在南方工作,每次一回家,人还在路上,就开始打电话,必要家里先给他买好夹肉饼,他下车就开吃。他说的夹肉饼是榆社特有的风味,别的地方吃不到。肉倒是常见,关键在饼。这是一种干面饼,制作的时候不加任何调料,不发酵、不油炸,是用大铁鏊子烙成,再入炉烧烤,清白微黄,外焦里嫩,十分好吃。榆社的邻县武乡和左权也有这种饼,但是做法和口味都不一,而且他们的饼都有发酵的成分,有或咸或甜的作料,不是这种最简单最原始的面饼,因此不及榆社的饼地道。
这种饼,我从小吃到大,那时候在二中念书,一早一晚上下学的时间一路上好多打饼的摊点,二中门口尤其多,它制作很简单,一个大铁炉,里面烧着炭,上面放一张大铁鏊。打饼师傅支一张案子,上面不是木头而是光滑的铁皮,铁皮上放着揉得光滑的面团,旁边是个小盘子,盛一些油。看到有人路过了,师傅就飞快地揉面,切一长条面揪成一个个剂子,两个剂子做一个饼,一个略大,压扁;一个略小,揉圆,圆的这个放到盛油的盘子里滚一圈,蘸得油汪汪地,放在那个扁剂子里面包好,再压扁,然后擀成一个圆圆的饼,就那样放在鏊子上,不刷油,一会儿就烙得微黄,泛出星星黑色的圆点,像虎皮,很漂亮;师傅把它们取下来,将鏊子揭起,小心翼翼地用铁筷子夹着面饼放在炉膛的边缘,略烤一会儿,饼就会像充气一样变得圆鼓鼓的,特别惹人喜爱。打饼的时候,师傅们会舞动擀杖敲击案板,并把面团摔得啪啪响,发出biangbiang的声音,清脆有力;每天清晨和傍晚,街边上都是这种biangbiang声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。我那时候特别爱吃一个瘦小的老人打的饼,积攒到几角钱就去买一只来吃。
打干面饼的摊位往往爱和卖卤肉、小菜的结伴,有的打饼人自己就兼营卤肉。卤肉一般是猪肉,有猪头肉、肘子和下水。古人说:百菜不如白菜,诸肉不如猪肉,这话很有道理;我也试过把牛羊肉夹在面饼里,确实没有猪肉好吃。我妹妹她们爱吃肘花,我则爱吃肥瘦相间的猪头肉。天色微黑的冬日黄昏,下班回家时路过这么一个小摊,远远就看到压好的肉垛子放在案子上,结结实实的一坨一坨,红红白白的肌理花纹像一层层火烧云,引得吃客垂涎三尺。案上一定置一把快刀,刃口薄而锋利,否则切下来的肉片太厚,口感就不一样了。称好肉,师傅挽一挽衣袖,操刀切肉,刀光霍霍,肉片纷飞,我以为这里应该换个动词,用“斫”,更为传神。最好等一个刚出炉的热面饼,只见师傅手臂一动,长柄铁铲一挥,啪的一声,饼已经落到了案上,他取刀在烧饼顶上划开一道口子,霎那间热气从那道狭缝中一涌而出,师傅快速将斫碎的肉片塞进去……吃吧,面饼酥脆,猪肉鲜美,浓香滚烫,让你舒服到心里去。不过小时候一般是吃不起夹肉饼的,我们通常只吃面饼,或者往饼里塞点小菜,就算是很难得的美味了,我喜欢把海蜇丝和腐竹塞来吃,一个只要三毛钱。
以肉夹饼这种形式,其实很普遍,以知名度而论,当属陕西肉夹馍为第一;现在榆社也有卖肉夹馍的,我吃过,很好吃,里面不是卤肉,而是肥美多汁的烧肉;但我以为不及榆社的夹肉饼,因为白吉馍太绵软了,烧肉又有点肥腻。风靡街头的洋快餐里也有类似的东西,汉堡包就是一种夹肉饼,我不爱吃,那种味道太粗放,不值一品。但是这些东西正在飞快地占领小城,大有超越干面饼并将之挤出小吃市场的架势——因为会打干面饼的人,真的越来越少了;肯寒来暑往早起晚归做小本生意的有几个呢?现在的街头,打饼的摊点只有寥寥数家了。
正宗的干面饼,首推迎春路上的任记,老有人排队买,面饼劲道,肉香浓郁。一天能打几大盆面,几百个饼。老板和老板娘都不多话,沉默亲切。我觉得开小店,就是要安静,呱噪着兜揽生意没什么意思,这样就很好。不过这饼的味道还是不及我当年在二中门口吃的饼,如今,那段日子已经是遥远的逝去的少年了——总的来说,上年纪的人卖的饼比年轻人做得好吃。
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好哪个医院看白癜风好